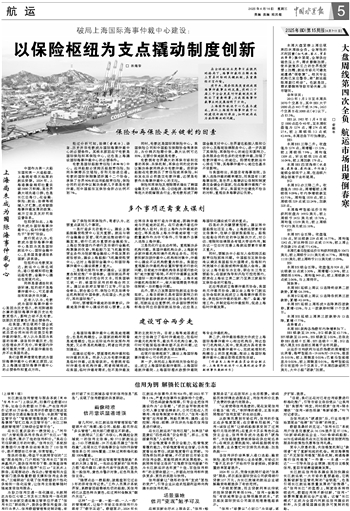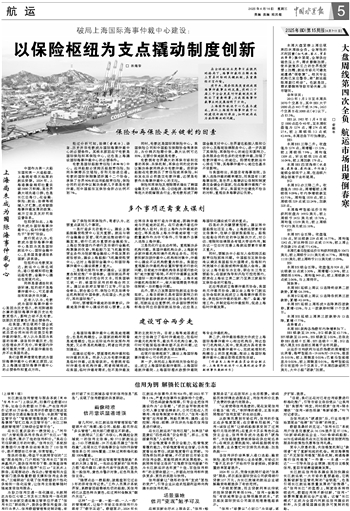□ 孙海华
在全球航运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格局下,海事仲裁作为解决海上贸易纠纷的关键机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海事仲裁事业的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更是对仲裁制度改革做出了重要部署,为我国海事仲裁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已基本建成,然而上海国际海事仲裁中心的建设却相对滞后,如何破局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上海尚未成为国际海事仲裁中心
中国作为第一大船东国和第一大造船国,上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航运资源。2024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000万标箱,是世界最大领先港口群,也是长江出海口,在金融、保险、航运、法律等领域人才汇聚,还有鼓励海事仲裁发展的政策、地方立法及友好司法监督体系。
但即便如此,上海仍未成为国际海事仲裁中心,临时仲裁也仅处于“首例”阶段。
流行观点认为,伦敦成为国际海事仲裁中心是因为其是国际航运中心、国际金融中心,且英国是普通法系国家、讲英语。
但纽约比伦敦更发达,航运中心排名领先,港口规模和吞吐量远超伦敦,金融中心建设也更现代化。
同样是普通法和英语环境,纽约却不是海事仲裁中心,可见普通法和英语并非关键。
还有人认为,伦敦成为国际海事仲裁中心是因为历史悠久,然而斯德哥尔摩的国际海事仲裁历史比伦敦更悠久,影响力却不及伦敦,说明历史因素也不是必要条件。
在我国,常出现两个国企或央企之间的大型船舶租赁合同或买卖合同纠纷约定提交伦敦仲裁的情况,有人认为是因为英国的法律、语言和仲裁历史,但这些理由并不充分,毕竟国内仲裁可能更方便,且英国仲裁法也并不比我国先进。
我们亟需弄清楚伦敦成为国际海事仲裁中心的真正原因,以及上海建设国际海事仲裁中心的必要条件和重点方向。
保险和再保险是关键制约因素
经过分析可知,法律(普通法)、语言、历史并非伦敦成为国际海事仲裁中心的必要条件。其根本原因在于伦敦是国际保险和再保险中心,这也是上海建设国际海事仲裁中心的必要条件。
伦敦是国际船舶责任险(保赔险)中心。远洋船舶必须购买船舶责任险,如同车辆需买交强险,否则无法进出港。伦敦的国际保赔集团所属十二个协会,承保了世界90%的远洋船舶责任险,保险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几乎都是伦敦仲裁,而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所占比例不到7%。
同时,伦敦还是国际再保险中心。我国保险公司和中国船东保赔协会等承保后,为分摊风险需分保,最大比例可达80%,主要分保地就是伦敦。
伦敦拥有世界最大的再保市场和完善的再保、共保机制,再保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同样多为伦敦仲裁。若所涉船舶在伦敦购买了责任险或再保险,纠纷发生后必然提交伦敦仲裁,这便是伦敦作为海事仲裁中心的支柱。
保险和再保险及理赔需求催生了跨国金融支付、船舶入级、公估检测、法律服务等庞大的配套服务行业,使伦敦形成了跨国金融支付中心、世界著名船舶入级和公估中心及海商法律服务中心,进一步巩固了其保险、再保险中心的地位和影响力,各类服务合同也多约定伦敦仲裁,加强了伦敦仲裁中心的地位。即便伦敦航运中心排名下降,其海事仲裁中心地位也基本不受影响。
与我国相比,英国没有海事法院,当事人选择仲裁的概率增加,而我国有11家海事法院,是世界上海事诉讼体制和制度最完备健全的国家,但在海事仲裁推广中常被忽视。所以,我国官方应避免不恰当的对标,重视自身海事诉讼优势。
多个事项还需重点谋划
除了保险和再保险外,笔者认为,还要重点谋划几个事项。
一是打造多元功能中心。建设上海船舶融资租赁中心至关重要。航运与银行金融融合紧密,现代航运推动银行金融变革,银行已成为重要的金融船东。上海应凭借国内外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聚集的优势,将船舶乃至飞机融资租赁业务作为陆家嘴金融核心升级发展的前沿板块,建设上海船舶/飞机融资租赁中心,这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海事仲裁中心建设都意义重大。
二是强化规则与意识建设。以国家意志制定推广中国条款。国际航运界有被广泛接受的示范合同文本,而我国缺乏统一的、被国际采用的标准合同文本。建议由政府主管部门主导,行业协会牵头,联合船公司、保险公司及法律专业机构制定中国条款,先在国企、央企推行,再向国际推广。
同时,要增强仲裁地的法律意识。仲裁地是仲裁中心建设的核心要素,上海应将自身培育打造为仲裁地,明确仲裁地与开庭地的区别。在引进境外著名仲裁机构入驻时,突出上海作为仲裁地的地位,将其选择上海为仲裁地审理一定数量案件作为许可条件,引导境外当事人选择上海仲裁。
三是优化行业生态布局。重视解决多机构问题。我国仲裁机构众多,上海就有多家仲裁机构和境外机构业务处。而伦敦和新加坡仲裁中心机构相对集中,仲裁中心建设不以机构数量为标志。我国应重视解决仲裁机构设置和管理的行政化问题,目前地方仲裁机构体系呈现行政化和“地方割据”格局,不利于仲裁事业发展和国际一流仲裁机构的创建。上海本地仲裁机构体制不一,做大做强需提早考虑体制统一后的整合问题。
此外,要大力发展国际性航运业协会组织。上海目前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性涉船涉航涉水航运业协会机构总部,而航运业注重惯例,许多国际惯例和标准合同出自国际航运协会,这应是上海国际化建设或引进的重点。
四是补齐关键要素短板。建议将中国船级社迁至上海。上海航运要素市场主体集中,但缺少国家级船级社。船级社检验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对公估、理赔和法律服务有强大带动作用,解决这一空白对完善上海航运要素市场意义重大。
同时,要解决中小船东入会即购买船舶责任险困难问题。中国船东互保协会难以满足我国船东大国需求,沿海和内河流域中小船舶或特种船舶入会难。建议以上海市船东为主体,联合长三角主要船东,在国家指导和风险可控范围内,探索在上海设立第二家乃至第三家船东互保协会的可能性。
还应考虑成立海事仲裁员协会,我国尚无仲裁员协会,建议由上海专门航运业协会组织发起成立上海海事仲裁员协会,承担临时仲裁的组织、推广、备案、管理工作,并制定临时仲裁规则,促进上海临时仲裁发展。
建设可分两步走
上海国际海事仲裁中心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机构概念。从国家战略布局看是地理概念,但从实际运作和发挥作用角度,又必然是机构概念,两者应同步规划建设。
在建设过程中,要厘清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的关系。很多人认为伦敦仲裁就是临时仲裁,这是错误的。伦敦既有临时仲裁也有机构仲裁,两者相辅相成。在我国,临时仲裁有需求,但不是仲裁发展的主流和方向。目前上海等地虽通过地方立法确立了临时仲裁地位,但临时仲裁无机构背书,裁决书无机构公章,执行时可能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这是推动临时仲裁的最大现实障碍。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建设上海国际海事仲裁中心可分两步走——
第一步,依托在上海的相关协会和企业,成立上海国际船舶仲裁院、上海国际港航仲裁院、上海国际潜水救捞仲裁院等专业仲裁机构。
第二步,待仲裁法修改允许成立上海国际海事仲裁中心相应机构后,将这些专门机构纳入其中,使其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专业海事仲裁中心,完成地理和机构概念上的双重构建,推动上海国际海事仲裁中心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
(作者系上海仲裁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促进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