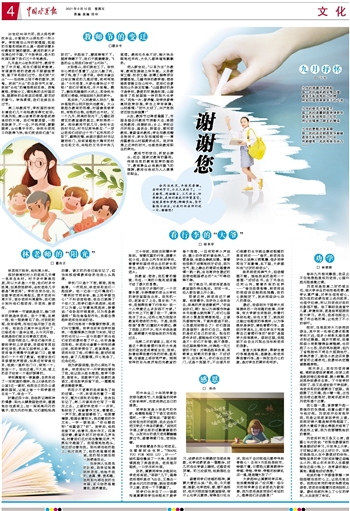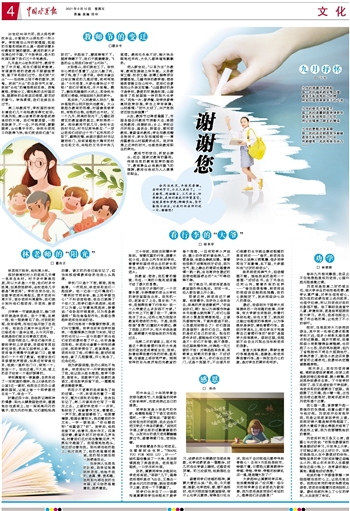□蔡永平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大山深处的一所小学。学校窝在山沟的皱褶里,扭曲的石墙和倾斜的土屋一起倾诉着乡村教育环境的窘困。教师的家大多在周边村子里,下午放学后,偌大的校园只剩下我们三个外地教师。
九月是大山收秋的时节,教师节放了半天假,师生们都回家割麦。有俩爱热闹的老教师不顾婆娘责骂,留下来和我们过节。我们抓“大头”——在纸单上写不等的数字,抓阄。抓到“大头”的自怨手气太背,抓到“白吃”的嘴角咧到耳旁。按阄缴钱,按能分工,情况熟的去村里买鸡,腿脚快的去商店买烟酒,厨艺好的掌勺。宰鸡煮酒,我们自娱自乐过节。
第二年教师节,学校里的徐校长请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帮忙收田。天高风轻,满山金黄的麦浪像波涛涌动的大海。我们弯腰屈膝,一把把拔麦子,不一会,汗流浃背,腰酸腿疼,头也晕乎乎的。徐校长老两口则拔得飞快,他们笑话我们是“白肋巴”。手起泡了,腰困得弯不下,腿疼得蹲不下,我们干脆躺着拔,飞扬的尘土把我们涂成“土行孙”。
太阳落山,我们就收工了。徐校长心疼我们累着了,让女儿割了肉,宰了鸡,做了一桌子菜。徐校长拿出过年女婿送的几瓶好酒,笑呵呵地说:“今天受累,大家也痛快过个节吧!”我们尽情地吃,尽兴地喝。醉了,躺在热腾腾的火炕上,和徐校长老两口唠嗑,恍惚回到久别的家中。
再后来,“人民教育人民办”,解决温饱的山民开始关注教育。大山掀起办教育的热潮,村里集资修学校,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木材。又一个九月,明亮的阳光下,几幢红砖青瓦的教室赫然挺立,学校焕然一新。那年教师节前几日,徐校长去找村书记,村书记爽快答应:“一定让老师们好好过个节!”红彤彤的夕阳下,戴鸭舌帽,斜披衣裳的村书记踱进校门,后面紧跟抬大羯羊的村主任和文书,年轻的文书手中拎几瓶酒。教师灶伙食不好,能大快朵颐地吃羊肉,大伙儿都幸福地飘飘然。
进入新世纪,“以县为主”办教育,教育发展驰上快车道。义务教育工程、校安工程、改薄工程等项目接踵落地,几幢伟岸的教学楼、宿舍楼昂首傲立在山沟中。老师们自豪地向山外亲友炫耀:“山里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最美的环境是校园,山里娃有了和城里娃一样的现代化学校。”两免一补、营养餐、助学贷款等惠民政策实施,学生上学有保障。山民感慨:“时代太好了,共产党把老百姓当亲娘舅!”
从此,教师节过得更隆重了,市里县里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奖励优秀教师、师德标兵;乡上、学校召开庆祝会、座谈会、联谊会,慰问老教师,看望退休教师;学生向教师赠自制贺卡,家长发祝福短信……尊师重教在山村里蔚然成风。我庆幸遇上这样的时代,也感受到教师职业的荣光。
教师节的变迁,折射出群众、社会、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相信在党的教育政策的推动下,教育事业必将展开腾飞的翅膀,教师也将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